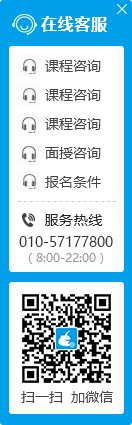(1)故杀。故杀的渊源已久,北魏时已经出现了故杀。北魏的《斗律》规定:“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杀子孙,五岁刑。殴杀者,四岁刑。若心有爱憎而故杀者,各加一等。”《隋律》中也有故杀,比如有“犯十恶及故杀人,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的规定。按《唐律》规定,故杀是“非因斗争,无事而杀”,即双方并非因为斗殴,一方突然起意杀人。这样,从前的贼杀就被新出现的故杀和单独进行的谋杀所分解了。以后明清都继承了唐律对故杀的这一定义,并对之进行更进一步的阐释,从而将谋杀和与谋杀关系最为密切的故杀这一概念相区别。
早在西晋,张斐对“故”的解释是“知而犯之”即明知故犯是“故”。因此,可以认为,谋杀、贼杀当然都包含于“故”杀人。西晋时期及以前的“故”均更强调主观意图,而谋杀和贼杀均更关注杀人行为的外部表征。也许正是因为“故”的这一含义的存在,所以,同属于故意杀人的谋杀和贼杀便各侧重于对其外部表征的描述以对二者相区别。但是后来“故”的含义最终演变成与“贼”相似,因此故杀这一新的杀人类型也取代了贼杀,而故杀和谋杀则成了一对需要认真区别的概念。法制史学家戴炎辉先生认为:“汉晋所谓贼杀伤,似相当于唐以后的故杀伤。”按照清代律学家的定义,故杀是临时起意的故意杀人。这种临时起意的故意杀人,其实正与英美法以及近代以来大陆法系区分谋杀和故杀的各国刑法中的“故杀”概念相同。
(2)谋杀。明、清两代法律中的“谋杀”概念渊源已久。在我国古代法中“谋杀”曾长期被看作是必要共犯。
战国至秦汉时期已经出现了谋杀这一法律概念。直到西晋时,才能看到对谋杀较为确定的解释。但此时对谋杀的解释仍是不完整与不准确的;因为西晋时的廷尉明法掾张斐并不是对“谋杀”这一概念本身进行解释,而是对理解“谋杀”这一概念具有关键意义的一个概念“谋”做出了解释。根据张斐的解释,“谋”是“二人对议”,如此一来,“谋杀”就应该是指二人以上事先预谋的故意杀人。张斐对“谋”的解释对于“谋杀”概念的发展、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从后来的《唐律疏议》中我们可以看到,谋杀首先被定义为二人以上的共同犯罪。但在《唐律》中谋杀的涵义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即谋杀不再是必要共犯,单独一人也可以成为谋杀罪的主体。因此,在唐代及以后的历代法典中,“谋杀人”条依然将谋杀看作是一种必要共犯,所以,为了对各行为人准确量刑,就有必要对共同谋杀行为人中共同犯罪人进行认定。明律继承了唐律的做法,在《大明律·名例律》中这样解释“谋”:“称‘谋’者,二人以上。”可见,明律仍然以为谋杀首先是二人以上共同犯罪。同时,明律也承认一个人也可以成为谋杀罪的主体,而且明律中对一个人进行的谋杀即单独谋杀的解释与唐律也基本相同。
到了清代,我国传统社会谋杀的概念已经定型。即谋杀是有预谋的故意杀人,而故杀是没有预谋、突然起意的故意杀人。有无事先预谋是区分谋杀和故杀的根本标准。同时,谋杀又包括共同谋杀和单独谋杀。如果故意杀人的主体为二人以上,因为二人以上的主体本身就是事先预谋的标志,所以二人以上故意杀人毋庸置疑为谋杀。这时,需要进行区分的便主要是单独谋杀与故杀,而区分单独谋杀与故杀的唯一标准则是事先预谋的存在与否,而恰恰是这一点有时很难认定。但是,显然,在传统法律的框架之内已经很难进一步解决这一问题。


 (1)故杀。故杀的渊源已久,北魏时已经出现了故杀。北魏的《斗律》规定:“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杀子孙,五岁刑。殴杀者,四岁刑。若心有爱憎而故杀者,各加一等。”《隋律》中也有故杀,比如有“犯十恶及故杀人,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的规定。按《唐律》规定,故杀是“非因斗争,无事而杀”,即双方并非因为斗殴,一方突然起意杀人。这样,从前的贼杀就被新出现的故杀和单独进行的谋杀所分解了。以后明清都继承了唐律对故杀的这一定义,并对之进行更进一步的阐释,从而将谋杀和与谋杀关系最为密切的故杀这一概念相区别。
(1)故杀。故杀的渊源已久,北魏时已经出现了故杀。北魏的《斗律》规定:“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杀子孙,五岁刑。殴杀者,四岁刑。若心有爱憎而故杀者,各加一等。”《隋律》中也有故杀,比如有“犯十恶及故杀人,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的规定。按《唐律》规定,故杀是“非因斗争,无事而杀”,即双方并非因为斗殴,一方突然起意杀人。这样,从前的贼杀就被新出现的故杀和单独进行的谋杀所分解了。以后明清都继承了唐律对故杀的这一定义,并对之进行更进一步的阐释,从而将谋杀和与谋杀关系最为密切的故杀这一概念相区别。